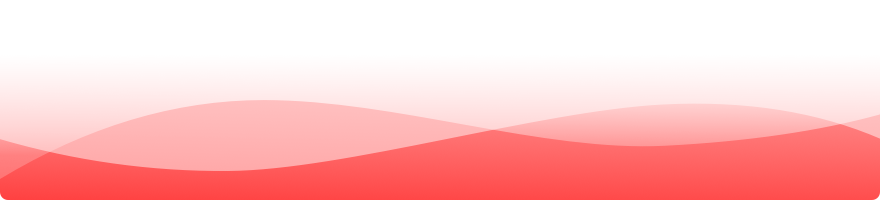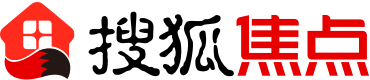严歌苓:爱情在最最美好的时候,都是带着疼痛的
扫描到手机,新闻随时看
扫一扫,用手机看文章
更加方便分享给朋友
【编者按】2018年6月13日,严歌苓老师再次来到水印书院,与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读者粉丝们,在水印书院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座谈会。这应该是近年来,严歌苓最深入的座谈之一。严歌苓老师从创作理念、作品解读到人生感悟,解答了读者们的众多疑惑。今日,水印书院发出经严歌苓老师审核后的座谈会文字整理实录,以飨读者。
真实的、面对面的沟通,永远比社交软件更精彩
标题:
走遍全世界,这里排在严歌苓最喜欢的地方第二位
我较大的愿望是:通过电影能够把更多的人带到书店里,多看书
孤独的人,内心有更多精彩有趣的秘密
跪着的,并不见得就是一个卑贱者
集体暴力的迫害,是几千年都没有断过
小说的意义,是留给读者和评论家去发现的
欧洲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人
移民其实就是一种“难民”
爱情在最最美好的时候都是带疼痛的
作家是一个很孤独的工作,所以我必须创造出一些“幺蛾子”来
我跟家庭妇女大妈聊天,也能聊出精彩有趣的东西
我从来不给评论家送书
热闹比宁静短,能力比欲望高,才能在出世入世间找到平衡
拓荒者,永远是很让我着迷的一群人
离开自然和自由,我就没有办法写作
我特别反感“女作家”这个词,“美女作家”就更恶心了
我厌恶战争,战争是非常无聊、很没必要的事情
对我影响较大的作家是马尔克斯
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,跟国外的人特别不一样
为什么大导演都在抢严歌苓的剧本
我觉得我在中国大陆得不了文学奖
(本文为超长文本,共16633字,预计阅读需要20分钟,请耐心阅读,你会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严歌苓)
山水间的对话
——严歌苓作品主题座谈会
时 间:2018年6月13日下午
地 点:中国 桂林水印书院
人 物:严歌苓、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师生、严歌苓团队
主持人:水印书院 陈炜
陈炜(水印书院 主持人):给歌苓老师介绍一下,这位是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黄伟林教授,然后这些都是年轻的学生,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。今天在歌苓老师很紧凑的行程里面,我们争取了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,她想跟一些年轻人见见面聊一聊天,所以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大胆的提。
那么在开始之前呢,我也要介绍一下,今天除了歌苓老师之外,还有歌苓老师非常强大的团队也来到了现场。这个是北京斑马谷文化的萧大忠先生,是专门做电影IP衍生品系列创意的;这位是杨劲松先生,是歌苓老师的文学及影视策划;这位刘稚小姐是歌苓老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。
关于广西师大文学院跟歌苓老师也简单介绍一下,广西师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2年,当时叫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,在抗战时期和西南师范学院还有昆明师范学院,被誉为中国抗日大后方的“西南民主堡垒”,它们在抗战期间保存了中国很大一部分的文化力量。所以桂林在某个角度来说,它有一段时间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的一个中心。所以桂林也有很多的文学文化的传承,包括我们看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的好书。
走遍全世界,这里排在严歌苓最喜欢的地方第二位
严歌苓:我在你们广西师大出版社出过一本书,时间很早,在01年还是02 年出版的叫《穗子物语》。
陈炜(水印书院 主持人):是的,所以说歌苓老师和桂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渊源。歌苓老师,排名前列个问题就是关于桂林的,您是一个走遍全世界的人,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,但在一年内来了三次咱们桂林水印书院,这是非常高的一个频率。延续今天早上咱们聊的内容,您说目前为止,水印书院是排在您全世界最喜欢地方的第二位。我想问歌苓老师这里给您的感受是什么?
严歌苓:我就是喜欢这个地方,觉得和水印书院的人和土地都有缘分,这里整个的气场跟我很对,当然了,食物也特别好吃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舒服。而且签售的时候才知道,原来在广西我有那么多的读者。桂林有很美丽的山水,山水是养人的,地灵才能人杰嘛,好山好水好儿好女。我觉得水印书院是能养眼睛、也能养灵魂的地方,当一个地方看上去非常心旷神怡,就一定会对我们的潜意识,和我们的精神世界产生滋养作用。所以我觉得以后要多来来这么好的地方。
陈炜(水印书院 主持人):是的,今天我们聊的时候共同讲了一个水印书院的关键词,叫“宁静”,桂林的山水会给人一种非常宁静的,能跟心灵连接的感觉。谢谢歌苓老师。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同学们。
我较大的愿望是:通过电影能够把更多的人带到书店里,多看书
王燕(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):我知道您的作品刚开始是因为电影和电视剧,然后开始对您的书感兴趣,在看的时候我会把电影电视剧和您的书对比起来看,通过这种对比我在想,这两种艺术方式可不可以互相考量?会不会有很多冲突?
严歌苓:冲突好像没有,我觉得每个作者都会认为,自己的作品里有一些非常天才的神来之笔,但是不见得改编的电影导演也会欣赏你认为的那个最最精彩的地方。还有呢,小说最精彩的地方是文字,还有心理活动、人的精神世界的展现、人的性格的展现,但这些在电影拍出来以后,根本见不到这个性格,也见不到文学描写里这些你认为自己写得还是很到位的地方。除了对话有的时候能搬进影视里去,其他的都很难的,所以说这两种艺术,只能是互补不会冲突。
不管怎样,我们的影视是一个大众媒体,有很大的观众群体,相比之下小说是一个小众媒体,而且现在越来越小众。当然我说的小说不包括那些网络上的消费文学,叫它文学呢也确实挺勉强的。
其实我较大的愿望是:通过电影能够把更多的人带到书店里,多看书。因为确实我觉得,我们国家的人对语言的追求、语言产生的艺术的追求一代比一代弱了。小说是语言产生的艺术,诗歌也是语言产生的艺术,当这些东西越来越变得小众,这就很值得我们警惕。别忘了中国是一个有非常好的文字、语言的国家,中文是特别特立的一种语言,再这样下去特别可惜。我希望通过我的影视作品,能够把更多的观众变成读者。
孤独的人,内心有更多精彩有趣的秘密
郭璐璐(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):您的作品里有很多最后变得非常孤独的人,如《芳华》里最后相互依靠的刘峰和何小萍。我在想这些孤独的人,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始终都是不能被理解的?
严歌苓:用萨特的话来说,他人皆地狱。一个人很难真正理解另外一个人,哪怕是你生活里很接近的人。我很多从发小开始就很亲近的朋友,他们根本没读过我的书,他们根本不知道严歌苓是谁。我跟我女儿也说过,你要是不读妈妈的书,你只了解一小半的妈妈。你看到的我,就是整天在家做饭啊,督促她做功课的这么一个普通家庭妇女。你不了解的另外一大半的妈妈在操心什么?操心的那些是跟人类很多、很大的命题是相关的,对吧?
文学确实是一种能够给予这种孤独的人帮助的方式,帮助我们走进他们的世界。其实人都非常的孤独,特别是西方国家,别看他们每天热热闹闹的打招呼,实际上,谁都不去看他们的内心世界。尤其是那些表面上显得比较另类的人,更没有人想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。
其实一个孤独的人,他内心的世界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,里面有很多的创伤,但是也有很多你想不到的、永远不被发现的很精彩的那种秘密。就像《芳华》里的何小曼,她把母亲的红绒毛衣拆下来染成黑色的,把红色的变成黑色,完全让它淹没在一个秘密里面,谁也不知道这件红毛衣的来龙去脉、最后的结局是什么,只有她一个人从头到尾知道,它是妈妈结婚时的红毛衣,最后经过这么多非常不公道,变成她妹妹的,而且这件毛衣是她爸爸留给她们少有的线索。所有的秘密都在把它染黑以后,变成了一个永远的秘密。
所以这些东西,就是秘密当中的那种有趣、不可思议的东西。我觉得我在文字里展示了这些秘密,实际上也就是展示了人性是多么丰富和复杂,永远不能简单用否定和肯定来鉴别。
跪着的,并不见得就是一个卑贱者
贾雅楠(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):我对《芳华》里您描写的集体暴力印象非常深刻,能把刘峰和何小曼的心理描写得这么细腻,我想老师应该是一个对善良很敏感的人。另外,通过阅读您对《少女小渔》和《扶桑》里海外华人生存境况的描写,我有一个疑问,我发现老师作品里一些女性,她们自身承受了很多难以言说的苦楚和苦难,我在读的时候会想,她们为什么会容忍这么多?会承受这么多?他们是怎么承受的?我不太能理解。所以今天正好有机会想问一下老师。另一个就是,今天海外华人的生存情况可能有一些变化,歌苓老师如何看待这种变化?有没有书写这种新变化的打算?
严歌苓:我现在不知道该写哪国的女性,因为我住过的国家很多,特别是当我年纪越来越大后就越来越发现,当你在一个国家住的时间不够长,靠着你想当然的方式,来写一个民族或者写一个地方的人的状态和内心,实际上是非常大胆的。我年轻的时候写《扶桑》敢跳到白人的心理,跳到白人的视角去写,现在我想我是肯定不敢这样做了。因为我发现,不同的人种和人种之间,其实永远有难以理解之处。我的先生是白人,即使我们已经结婚快30年了,用一种形容,就是我们在语言和感觉上仍然有很多“美妙的错位”。讲一些很简单的例子,你看外国人很多动作是跟我们相反的,剥香蕉他们从这头剥,我们从那头剥。很多时候你觉得,我说了这句话他该生气了,但他不生气,你说了一句你觉得很平常的话,他反倒生气了,觉得你冒犯他了......所以到现在呢,我就觉得要写好一个民族的人,要一定要在那住很长时间,对那个语言和文化要很了解很了解才能写。
关于海外华人,怎么说呢,不知道为什么04年离开了美国以后,我就很少再去写那一类作品了。可能因为是我现在对中国当代,现在产生的社会变化、形成的新的阶层,还有各种阶层的人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特别感兴趣,我觉得我们国家这30年的变化是较大最激烈的,这个东西是特别值得一个作家去写的。
关于你说的女人的那种承受力。这个承受力说的不是现在城市里的女人,我写的很多都是最底层的女人,像《扶桑》、《金陵十三钗》,她们是妓女,是最底层的底层,像《小姨多鹤》这样的一个家庭。用赛珍珠(Pearl S. Buck)的话来形容就是——她从来没有发现哪一种人像中国女人这样,有一种彻底的接受的态度,对生活、对命运、对她周围的遭遇也好,她有一种彻底的接受。这种接受的同时就是宽容,就是忍耐,也是无奈、也就是乐观。为什么说是乐观?因为她们可以这样子生活下去,说明这种悲惨的生活里,她们照样可以有她们的乐子对吧?如果有一种人完全没有乐子,这种人会灭绝的对吧?如果她还能生生不息,证明她是有乐子的。
我过去的婆婆,她多次的提到她小的时候,大概五六岁吧就帮着家里推磨,她就特别羡慕在外面玩的孩子。那她怎么找乐子呢?她就自己一边推磨,一边玩自己拿笤帚做的小人,玩让他们走亲戚啊什么的。还有一次她说,有一天驴往后退了几步,把她的几个脚趾盖都踩掉了,但她也没觉得多么疼啊?就是这样的一个要劳动不能去外边玩,只能自己和自己玩的一个小姑娘,她提到这些场景的时候,你能体会到她的那种童真,和在这种劳动当中被异化的一种孩子。这样一个农村的姑娘,她长大以后虽然变成了一个伟大作家李准的太太,她也仍然没有抱怨,她没说我以前的生活多苦。
所以中国的女人非常伟大,还有日本女人、亚洲女人其实都是蛮伟大的,她们那种包容和对生命的一种接纳的态度,就是你欺负不了她,你也伤害不了她,因为她的接纳本身就包含了对男人的原谅,对男人的宽容。很多时候,她们像是我在《扶桑》里写的一句话:“扶桑跪着,却宽容了所有站着的人们。”所以跪着的,并不见得就是一个卑贱者。
集体暴力的迫害,是几千年都没有断过的
陈炜(水印书院 主持人):刚才这位同学还提了一个词“集体暴力”,可能在她们这个年代,集体暴力是不太能感受的到东西。
严歌苓:有啊,网络上现在也经常集体攻击某个人,这就是集体暴力,就是人性里的迫害性。迫害是人性当中所包含的一种元素,这种元素一旦失去了法律的约束,不把这个人性用拴狗绳拴住了,一旦放出去以后就会就变成失控,一发不可收拾。像我们的文革,像南京大屠杀因为战争给了一个机会,一下子把那个牵狗绳给松开了,然后那种非常黑暗的,莫名其妙到已经上升到形而上的一种破坏欲就出现了,这就是我们人性当中的弱点。
人性当中很多弱点,但你要站得更高一点来看的话,其实他也很可怜。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暴力?是不是他跟着一个集体去迫害一个人的时候,他就忽然觉得他优越了?还有就是我跟着集体走,我是安全的,对吧?哪怕是跟着集体残害一个人,他也认为在这个集体里,他是安全的。比如说把老舍最后逼到去跳湖的是他的家人,他的家人最后对他不接纳,参与到社会这种大集体里一块来迫害他,来找寻找一种安全感,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。宗教上也发生过很多次这种迫害,德裔瑞士移民有一只宗教叫阿米什(Amish),为什么会全部迁移到美国去,也是被迫害的原因对吧?所以集体暴力、人性里的迫害欲是几千年都没有断过的。
小说的意义,是留给读者和评论家去发现的
王云杉(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):我注意到您在小说里面都给了人物一个逃离的这么一个命运,或者说隐藏的一个命运,就比如说《第九个寡妇》里,王葡萄隐藏她公爹的地方,后来也成为了一个寡妇儿媳的藏身之地;《金陵十三钗》里女学生她也是躲到了那个教堂里面;《陆犯焉识》它也涉及到这种人物的逃避逃离的命运。请问一下老师,您写的这种人物的命运模式有什么样的一个含义?像那个爱丽丝门罗(Alice Munro)她也写过逃离,那么这个这种逃离,或者说是自我隐藏的命运,它有什么样的深意?
严歌苓:我还给你提醒一下,《小姨多鹤》也是一个藏在中国人家的一个敌人的女儿,对吧?因为我不是个理论家,我不可能回答说它的具体意义是什么,小说家是搞形象思维的人,很多东西她写出来后,并不能非常清晰的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写。所以有关藏匿的、或者逃离的这些东西,也许在我的潜意识世界里面,我可能是Fantasize(幻想)一种躲藏一种逃离。
我认识一个电影导演,他特别喜欢窥视的视角,对窥视就特别有一种偏好,他喜欢用一个不知道谁的主观视觉,在看这个故事,在看人物,他说任何镜头从窥视的角度看都特别动人。他提到《金陵十三钗》如果是通过一个小女孩,就是书娟的窥视来展现这个故事,这个故事就会更动人。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。
所以我觉得,你是学文学鉴赏的,学理论课的时候你就要去分析这个作品的意义是什么?如果有八个评论家,同一件事情大概就会有八个对你的分析,他们认为你这样写你肯定有这样一种意义在里面。所以意义,肯定是留给读者和评论家去发现的。如果一个作家出来讲:我的小说就这意义那个意义......我觉得这种人肯定不会写小说,这个人就肯定是一个干扁透顶,干巴到家了的人,对吧?
欧洲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人
王云杉(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):您曾经长时间生活在美国,请问美国文化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?
严歌苓:美国文化......首先美国有很多很好的作家,我读过他们很多小说,特别是有一个39岁就死了的女作家,叫弗兰纳里·奥康纳(Mary Flannery O'Connor ),她写的特别好,特别美国式的、美国南方的那种感觉,她不是被很多人知道,但她确实写得特别的美国式文化,这才是美国文化。
大陆的旅游团跑到美国去,把比如Las Vegas那种非常物欲的、非常明朗而浅薄的当成美国文化;还有一个美国的电影里面讲的,美国人是什么人?就像一团美国奶油,又厚又黏又油腻而无味。所以美国文化究竟是什么?我觉得我也还没有特别清楚的认识,我只是觉得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地方,我最开始为什么选择到美国去留学,就是因为我看到美国人的那种敢于推翻,敢于质疑的那种较大程度的自由。当然,我现在发现欧洲更自由,美国政治正确其实还是挺厉害的,欧洲人反而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。
移民其实就是一种“难民”
谭凯匀(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):我想就《扶桑》这本小说提一个问题,因为我在阅读时感觉扶桑是一个符号性的形象,她不太出声,都是阐述者在代言,把她描述成一个类似于圣母一样的形象,您是有意把她处理成一个符号性的形象吗?
严歌苓:《扶桑》这部小说,本身来讲也比较形而上一些, 比较抽象一点。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形式跟扶桑对话?和她对话的其实是一个女作者,一个当代的新移民。我就想用这个形式来写它,因为这段历史如果不这么写的话,你想想,它好看吗?我觉得不会很好看,会是一个比较陈旧的历史故事而已。我就是通过扶桑把移民的这种女性和移民的“难民性”做表达。
移民其实就是一种“难民”,因为移民永远带着一种难民的潜意识在生活,不干活就不行,不挣钱就恐慌。然后很多的移民的女人,会嫁给这个国土上的原著民,比如美国人,比如那些比她们更早去那儿的,“难民”意识已经比较薄的那种人,所以这就是移民女人。
移民其实是很不幸的一种现象,一个人,不管他是哪一个民族,他在自己国家如果混得好,他是不会移民的。比如说爱尔兰有一年的土豆忽然发生了灾害,没有办法活下去了,然后就有了爱尔兰移民。像我们这些当年的留学生也是,后来的移民在中国的经济起来的那段就变得少了,对吧?
我就觉得呢,移民是一种因为迁移,还有一种叫Displaced(流离失所)以后的心理创伤,因为你是一个暂时不能跟人家有任何的竞争力的这样一种人,语言上的能力也很幼稚,甚至不懂,所以移民应该说是一种悲剧的、创伤性的经历。那么移民当中的女人,就更加的有创伤性,因为她们通常会想到去跟什么人有婚姻,能够使她这个地位迅速稳定下来,很多很多的女人都是因为这样,非常委屈地嫁给了外族人,然后很多的结局也都是比较悲惨的。
爱情在最最美好的时候都是带疼痛的
严歌苓:所以我了解了这些以后呢,我就觉得扶桑这样的人,其实她是一个非常例外的移民,她嫁给一个马上要处死的人,这样她有了一个结过婚的人,她还能去享受她较大程度的自由。而且,扶桑把爱情看成一种伤害。就是不管你爱,或者是盼着被爱,都是疼痛的。她嫁给了大勇这样一个已经被送上绞刑架的人,她便认为她即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,爱情就再也不会来伤害她。爱情这个东西——除非你是那种特别狂热特别有激情的爱情况下,其实爱情在最最美好的时候都是带疼痛的,所以扶桑不想要这种疼痛。
扶桑是一个很例外的人,她觉得即使当妓女也没有什么。你认为要解放她,可她不觉得她需要解放阿,甚至她会觉得比你们那个教会的、学校里的那些没有自由的人,她认为她还活得更好一点。而且她享受性,因为她缺乏耻辱感。妓女、强奸或者被迫的那种性关系,实际上是我们有了文字,文字创造了概念以后,才使我们觉得强奸、妓女这些概念都是特别疼痛的。这些概念放在女人身上,女人会觉得非常非常疼痛和耻辱的。但是扶桑这个人缺乏概念,她是一个好像从远古来的人,她对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概念,她会去享受这个性爱。
所以《扶桑》是非常的形而上的,扶桑这个名字本身就是这样,“此去扶桑东更东”,就是东边再往东、一直往东,扶桑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有很大的象征,她就是象征着东方。
作家是一个很孤独的工作,所以我必须创造出一些“幺蛾子”来
张冬英(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):您的大部分作品,勾勒的都是历史发展途径,将历史内化成个人的生命体验,写出主角的心灵情感史。但是这些作品中其实有些人物和你的生活是非常接近的,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在创作中能保持一种距离,不被牵着走,把您和您的主角(就是叙述者)隔离开来的?
严歌苓:我觉得我现在写作已经蛮自由的,我想写成什么样就写成什么。比如说《芳华》,最开始我也没有去想这个形式是什么样的,但是写着写着,就自己出来一种非常自由的风格。我既是小说中的穗子,也是小说外的严歌苓,严歌苓和穗子实际上是既是一个人,也是不同的,有虚构的也有现实的东西。
我就觉得,我已经不再考虑现实和真实的“我”,与这个虚构的人物“我”有什么区别,我不再考虑要用什么写作技巧去把它区分得非常清楚,我也不再考虑这种设计是什么目的……我没有目的!我怎么写的,书就怎么来。我只想这一篇和上一篇不一样,我就这么写! 因为假如小说的形式老是一种写法,语气老是一种语气,我就会感到很沉闷,没意思。
作家是一个很孤独的工作,对吧?如果觉得这篇写作我没什么创新,我就觉得很闷,所以我就必须要创造一些,就是北京人所谓的“幺蛾子”出来,一些跟过去肯定不一样的东西,让它有很大的变化,这就是我选择的一个写法。
但是这种写法,也不是我排名前列次这样写,我很喜欢这种人物在虚拟和现实里出出进进,非常自由的这种写法。《扶桑》里也有一点类似的东西,它有纯粹客观的,也有主观的,一半一半吧。还有《陆犯焉识》,看起来是个第三人称的小说,但是这个孙女她不时的出来一下,这时她就是陆焉识,她就是我爷爷,是吧?用那种嬉笑怒骂的语言,不当真的那种语言,诠释了陆犯焉识里很多很多的灾难。比如说梁葫芦被马倒着拖把头皮脱掉以后,他就说梁葫芦正面看还是梁葫芦,后面看却已经是一枚骷髅了,有一部分他的头就变成了骷髅。
那这种方式呢,都是这个孙女在诠释他爷爷的这段苦难。因为一个八十年代的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子,她对这种苦难只会觉得不可思议: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?这么荒诞的事情?如果她还来一本正经跟你讲这个故事,这就显得很愚蠢。所以我就用这么一个孙女来讲述爷爷的故事。
我跟家庭妇女大妈聊天,也能聊出精彩有趣的东西
陆立伟(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):排名前列个问题,我想了解一下,西方的文学理论对您创作有影响么?第二个问题,是现在国内的文学研究界、评论家他们对您的作品的观点、他们的评论文章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么?
严歌苓:我不看这些文学创作理论的书啊,我看了会看僵掉的!我觉得一个小说家还是要多看看自然,多注意一下你身边的人物。哪怕是听听家庭妇女的故事,都比看那种理论书要有意义。因为一个好的小说家,他的形象思维会非常的丰富,自会从他的小说里,提炼出一种他认为该传达的意义,就是形而上的东西。
美国有很多how to ......这一类引导你怎么去生活的指南书,比如说你怎么样变成你们家的一个修理员,你怎么变成你们家的一个会计师,叫how to book,how to do what..系列的书。当然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这些这些书,后来我发现这一类的书,实际上并不能让我对世界的认识产生太大的影响,所以我不再看了。
文学创作理论类的书也一样,翻了几页以后,我觉得读起来还是蛮辛苦的。而且我也不想去把自己搞得很高深,特别是年纪大了,越来越觉得诚实是最重要的。诚实,就是你对学术、你对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,是个什么样的作家,必须保持一个很诚实的态度。不能因为读了那两本书,可以把严歌苓这样一个作家改变成另外一个作家。
我觉得作家对生活的了解,就是对各种各样人的生活的了解,生活是是小说的源泉。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啰嗦很啰嗦的朋友,是一个家庭妇女。但是呢,我总是要听下去,因为她的话里总是会有那么一些非常精彩的、你根本想不到的细节。所以我可以听她一两个小时的废话,但是只要在其中找到那么一个细节,我就觉得非常值得。
她跟我讲了这么一个事儿,她说如果谁谁谁的爸爸来跟你借钱,你可千万别借给他啊,他虽然是个老教授,但他会拿这个钱去赌博的。她说这个老教授跑到美国来,每次去赌博会拿一个塑料袋子,把三明治非常整齐的放到塑料袋里,然后带去赌博,赌一天就吃那三份三明治。这个老教授赌博的感觉就是特别郑重,就像去上个班似的。然后赌博回来后呢,再很省的把那个装三明治的塑料袋子洗洗挂起来,晾干明天接着用。我觉得这些细节特别能够体现一个规规矩矩的教授,一个知识分子当他变成赌徒以后,他即使已经狂热,内心已经疯掉了,但是他的赌博的细节,会和一个黑社会的赌徒不一样,会和一个一般的工人赌徒不一样,对吧?他是个教授,所以他拎着一个公文包,装着三份三明治像上班一样去赌博。回来以后他还舍不得把这个装三明治的塑料袋丢掉,他把它洗干净夹在一根铁丝上面晾干再用。就是这样的细节,一下子就把一个规规矩矩的知识分子、一个原来很洁身自好的人,变成一个不知归途的赌徒后的形象立起来了,对吧?这种细节,如果这个啰嗦的家庭妇女朋友不告诉我,我自己去凭空想象一个教授怎么去赌博,我是想不出来的。
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当代的思想潮流,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形而上的这个角度来认识世界、社会还有人。但是我觉得我不适合这种方式,我适合的就是听,听听大家聊天,去看活生生的东西。我不缺少理论水平,我需要的是活生生的东西。
我从来不给评论家送书
严歌苓:关于对我的作品的评论呢,我很喜欢看年轻评论家的文章,比如说是博士生啊、硕士生啊写的文章,因为我觉得他们写起来是没有负担的。在中国很多人习惯找评论家写东西,你还得去跟他们打个招呼:“帮我写篇东西吧”什么的。但我从来不会求人,我从来不会说我新书出来了,很主动的给某个评论家送一本,特别不会的。如果他感兴趣他自然会写,他如果觉得我的某本小说,在社会上产生了足够大的影响引发他的关注的话,那他自然会去找这本书看,对吧?但是我特别不会去给评论家送本书啊什么的,在我的价值观里,我总觉得做小说家要自由一些,清高一些。
热闹比宁静短,能力比欲望高,才能在出世入世间找到平衡
陈炜(水印书院 主持人):作家张翎有一句话:“有严歌苓的时代,是幸运也是不幸的,她让我们所有人都黯然失色”。她说,相比张爱玲晚年那种萧索和黯然,严歌苓在出世和入世之间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平衡,这是她对你的一个看法或者一个角度的解读。实际上,因为我和您接触比较多,我也观察到很多不同状态的您,比如说像在这样的一个场合,您会认真去谈很多的关于创作啊思维啊阅历啊等等。在朋友间私下聚会的时候,也看到您有很天真很开心的一面,唱歌、兴之所至席间起舞,甚至激动时会挥舞拳头说“我要做一个解放者!”这样的一些很可爱的场景出现。这种严肃和率性的平衡,实际上在中国是蛮难得的一种能力。
严歌苓:但是你看,我回德国就等于出世了嘛,因为没那么多朋友,有的就是书啊电影啊狗啊孩子啊这些东西,所以基本上就是非常沉潜的心,非常沉潜的一种状态。可以好好的大量的很自由的读书,可以有大量的时间写作,生活都完全在我自己的控制之下。每天的内容也都是填得很满很有方向性,今天要写多少,要读什么书,哪几本书要快点读掉,这些都是可以自我设定的。
虽然说这一种状态也不算出世,但是跟中国现代的这种忙忙碌碌,在上海或者北京,每个人你看他们失魂落魄的,和我聊的时候都好像目无定珠,每个人都忙得好像天天都有一大堆的事要谈要处理。如果我在这种状态,我可能十天后肯定就要疯掉了。
当然我出世和入世的这个比例,出世或者说这种寂寞的状态太久了也不行,对吧?脱离太久了,你不知道国内人现在在想什么做什么,这也不行。另一方面如果入世的时间太长,十天后我肯定也是受不了要发牢骚了。出世入世的比例得对,就是宁静的时间长,然后热闹的时间短。
还有我觉得,我总结出来我自己比较喜欢换的状态,是对自己满足,比较喜欢自己的这个状态。比如说我的才能有这么高,相比之下欲望就得低一些。你也不能老够不着那个欲望,如果你的欲望比起比你挣钱的能力、出书的能力、比你有名的能力都要多出这么多,那你够不着时就特痛苦。所以我现在活的就是现在这个状态,就是我的能力要是这么高的话,我的欲望相比低一些,我就觉得我很宽裕,也就比较开心。
拓荒者,永远是很让我着迷的一群人
黄伟林(广西师大文学院教授):我觉得您在中国作家里边是比较特别的,一方面从时间上可能您对整个中国20世纪很多历史时期都有很深入的描写,另一方面从地域上写过的地域覆盖面也非常大。刚才您也谈到您和您女儿说妈妈在做的事情、写作是与人类的很大的命题相关的,是吧?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期待,我想了解一下您后面写作上在这方面有些什么考虑?
严歌苓:我当然还有一系列的作品,在这个阶段都还在做资料搜集。比如说梅兰芳的故事,我就很喜欢。他这一生的这个戏中人、人中戏,这种女中男、男中女的现象,我觉得应该是很有趣、很神秘的。还有我觉得1988年海南刚搞建设开放的时间,当时的“闯海人”的故事我也很喜欢,但是现在都是苦于了解的还不够,还不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去写了,所以我现在还在做资料研究。
不仅仅是“闯海人”这样的一种经历,实际上我觉得开拓者拓荒者,永远是一种很让我着迷的一群人。他们甭管什么情况都要走向未知,走向没有航标的一个航行。早先我很崇拜哥伦布和麦哲伦,他们发现海峡穿过去以后两个大洋是连在一起的,发现新大陆,发现世界是个圆是可以走通的......这种人都是喜欢走向未知、去探知未知的,这种人的精神是极其的英勇的。所以“闯海人”让我感动,就是“成败皆英雄”,因为这种开拓和闯荡,已经就是一种英雄的品格了,当时内地有10万人踏上海南的时候,他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等着他们。美国人常说当你在你呆的地方待不下去了,你就向西边走吧,那么“闯海人”往西海岸走的这种精神,就像美国当年的西部大开发精神一样,我特别赞赏。
离开自然和自由,我就没有办法写作
黄伟林(广西师大文学院教授):我听说您对海明威抗战期间到桂林的这段历史有兴趣,您的作品涉及到抗战这个历史时期也蛮多。在抗战时期,桂林在中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,也有非常多的题材可写,海明威其实在桂林只是一个过客,在桂林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故事。如果有可能,我们真的希望以后您能创作一部桂林题材的长篇小说。
严歌苓:朋友曾给我发来海明威妻子玛莎 · 盖尔霍恩(Martha Gellhorn)的一本书《我和一个人的旅行》(Travels withMyself and Another),一部纪实的作品,就是海明威的妻子她陪着他到桂林来什么的。这本游记中有关于玛莎 · 盖尔霍恩陪同海明威,在1941年抗日战争期间桂林之行的记述,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,一个外国作家正好遭遇了中国的世界大战,这些旅行里发生的故事,成了了解那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。这种有趣的故事,很有可能就是我下一次创作的源起。
但我的创作是一个特别自然的现象,离开自然和自由,我就没有办法写,你不可以强迫自己去写,只能是看你能不能写。比较幸运的是,别人托人转给我的资料呢,因为我这个人兴趣特别广泛,我都会去看,很多时候也能发现当中的可以写成作品的亮点、看点。当然也不会马上就可以写成作品,因为这不是命题作文。有的时候尽管你做了很多资料,然后完了还是没法写。有的时候也许也会你做着做着研究,你会发现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故事。
我特别反感人家说“女作家”,“美女作家”就更恶心了
潘女士(读者):说到歌苓老师,大家都说您是“女性作家”里的代表,其实在我看来,不能用“女性作家”这个概念,在整个文学作家体系里面去定义和衡量歌苓老师的地位。我觉得歌苓老师经历过战火,见过生死,这些经历都是中国当代作家里面几乎没有过的体验。我觉得这种体验会给歌苓老师一种特别的滋养和力量,因为我觉得您作品的题材与广度,从历史的角度,从人性的角度,人类的角度里面,都是很多男性作家达不到的,甚至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都没有这样的高度。那么我想问的是,你是从哪里获得这样的力量和高度,在你的小说里去呈现这样的宏大的史诗般场景的题材?
严歌苓:过奖了。我觉得,怎么说呢?我特别反感人家说“女作家”,我说我不就坐在这,你还用在我前面再加个女作家吗?“美女作家”就更恶心了对吧?你讲得对,不应该把什么男作家女作家做这种分类,还有什么“华语作家”,就用这个词说明你不住在中国的是吧?如果搞理论的人最后就搞出这点名堂来,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悲。
因为我的人生经历确实和其他人不太一样,我12岁就当兵了,所以很早就接触生死。比如说入伍排名前列年我们就去西藏演出,西藏当时刚刚有一些冲突,所以我们每个班都要有枪,两支长枪一支短枪,加上当年的川藏路简直难走的不得了,所以我们每个人上高原之前,都要写一封遗书,也像是决心书血书那样的一种东西。
每年我们上高原六次,每次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险,哪怕是去上厕所。大雪封山时上厕所难,男孩去那边雪地女孩去那边雪地,雪地就是我们的厕所。积雪非常深,你要把雪扒开才能蹲下去,要不然你屁股就坐到雪里去了。扒那个雪的时候,就扒出很多比如说摔扁的钢精锅阿、勺子阿,还有什么衣服一箱一箱的,还有人扒拉着呢还不一定会扒拉出什么来。是怎么回事呢?说是哪个汽车团翻车翻下来,就掉在这底下了。因为当时那个路很差简直就没办法走,当时运送物资的运输兵牺牲的很多。坐车时经常我都不敢睁着眼看,坐车上看它是完全就是在悬崖边上悬空走的。如果遇上会车,车要退很远,直到一个稍微宽的地方再慢慢过去。
如果一个12岁的小姑娘,从这么小就要考虑到死或者危险,那我觉得肯定从她的潜意识里,她就已经是不再是个小女孩了。
我厌恶战争,战争是非常无聊、很没必要的事情
贾雅楠(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):老师我比较好奇,我在看您作品的时候,涉及到一些战争场面的描写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《芳华》里的刘峰在流血,然后成千上万的红蚁,排着队似的走向他的身体。我想问一下老师,在写这些文字上描写比较残忍的场面的时候,是基于老师您自己的想象还是真实的体验?
严歌苓:这是真实的,但不是胳膊是下巴,那个人的下巴给炸掉了。然后他一路爬回去,脸上满脸都是红蚁。在写这些残酷场面的时候,想象力我还是有的,但较好就别让我看见,有时候还没办法亲眼看,你看美国电影多残酷,特别可怕。但是战争就包含着大量这样的画面,一个小说家对战争的态度,如果没有这些画面的话表现不出来。我厌恶战争,觉得战争是一个非常无聊、很没必要的事情。我经常跟我先生说,为什么不能发明那种长时间的麻醉药,像打大象那种,睡着了倒下来了以后,你就把他俘虏了不就完了,你何必把人家都杀掉干嘛?所以我想我得和一个麻醉专家发明这种药申请专利,你说有什么必要非要杀伤人杀死人?失去战斗力就可以了。
陈炜(水印书院 主持人):歌苓老师在创作时,写东西的时候,收集素材体验生活的过程中,她对自己挺狠,我听过很多艰辛的故事。但我觉得,她对她自己作品里边的人更狠。每次我看她的书都很难受,看完一本得隔一段时间才能看下一本,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阅读。
对我影响较大的作家,是马尔克斯
王云杉(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):您认为写小说这件事情,可不可以通过讲授,或者通过教授来让学生掌握?因为现在有些学校它有一个创意写作中心,北师大复旦都有。我们在学校里面也在学习怎么读小说,怎么来分析小说。您觉得写小说能不能教?作家能不能教授出来?
严歌苓:我觉得可以教,但是这个学生,排名前列他要有小说家的潜质,你得知道什么故事写出来是小说,什么故事写出来就是一社会传言是吧?第二我认为他一定要去社会上生活几年。比如说我读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的硕士的时候已经是30岁了,在社会上已经有很长时间的经历。如果你在大学就直接去学写作,没有什么经历,按一般的道理来讲,生活阅历几乎完全是一张白纸,那肯定是写不出什么东西来的。
你找二手货,在网络上的奇奇怪怪的事件里去写,那么你的体验也不可能对,因为你要写的这个人你都不能站在他的鞋子里看世界,你怎么可以写得好?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在社会里自己滚打,在那泡,将来才有可写的东西,即使你的经历没有可写的,你也会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题材。
当然,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写小说的题材,但是你的人生的体验必须是真实的,比如说普鲁斯特写《追忆似水年华》,写了50多页这个人还没起床呢,这种也是好小说对吧?应该说是经典式的那种写作,他的心理体验是非常的真切、非常细腻的。他这么一写,你看的时候就觉得,哎呦,我就完全能知道他的那个感觉是什么。如果你不在社会上走一走,没有接触到足够的人进行采样,你怎么能写出这样丰富,这样细腻的感觉呢?当然,除了写《简爱》、《呼啸山庄》等书的勃朗特三姐妹的那种天才,写作时她们压根就没接触过什么社会,没谈过恋爱,全是想象出来的。
王云杉(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):谢谢老师,对您影响较大的作家,您觉得是谁?
严歌苓:对我影响较大的作家,是马尔克斯。因为我看了他渐变的过程。他从一个写实主义作家,非常的左派,非常同情普罗大众的这么一个作家,逐渐逐渐变成魔幻现实主义,其实他始终写的还是那么几件事。后来他的那本自传《Living to Tell the Tale》(活着为了讲述)里面还是讲到他小镇那些人,他和他妈妈回去卖那个房子......就这样一路。所以我就知道了,一个人他能够从现实的写法起飞了,飞起来了,然后呢,你又可以完全找到它的这种特别真切的真实。虽然他写法已经是魔幻了,已经抽象、抽离开了,但是你仍然能够看到他抽象上的一种真实,一种比真实更高的一种真实,我觉得这个人是非常天才的。
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,跟国外的人特别不一样
张冬英(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):我觉得歌苓老师的作品里,反映的女性形象有个比较突出的特征,很多是被侮辱、受迫害的、最底层的,给我们的冲击力特别强。我想问问老师,你对男性和女性在现今或是历史上,男女关系的互动上面怎么看待?
严歌苓: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命题(笑)。反正我觉得吧,在中国这种互动都是很……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,跟国外的人特别不一样。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是用责怪的、抱怨的方式,来表达他对你的关注和关心。比如她在前面走,“啪”的撞到那个玻璃上,他就会说:“你TM瞎啊!”,其实他是心疼她撞到头了的。当然呢,如果他是她的情人,也可能就不会这么粗暴。
现在很多中国男人富起来了,他明明表达感情的方式很多,但这个很富有的男人他就要给你买东西,你要是不让他给你买,他会觉得我怎么对你表达爱呢?反过来如果是一个女人特别有钱,男的是没有什么钱的,这个男的就都呆不住了。如果反过来女的给一个男的买东西,这个男的就觉得特别找不到范儿,上个床都不行这种感觉。就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性的暗示,谁是排名前列者谁是第二者,谁是拥有者谁是被拥有者。
所以我也无法解释,我觉得我也在探索当中。我跟我的先生打交道,他是西方人,他们听到的都是你话里字面上的意思。比如说我跟他去买东西,从超市走出来,他拎着两个比较轻的包,然后我拎着大概四个重包在后边走,我当然跟不上了。然后他一回头说:”Are you OK?”我就恶狠狠的说:“I’m OK!”。他会觉得你说OK了,那就是OK了对吧?那就继续走。一直到我说:不OK!他说不OK你为什么不早说?我说你眼睛呢,你不看吗?没看到我拿着这么重的东西么?当然现在已经习惯了,有什么就跟他正面直接讲。他问我累不累,废话我能不累吗?我给你做那么一桌子饭,我现在就会说是有点累,就是这样子。还有的时候我会说:你刚才讲的那句话,我听了很不高兴,你以后能不能不要那么说话?这样他能很接受,马上这件不高兴的事情就摊开了,我也就不会再怄。
他不会读女人,比如说我有一次跟他吵架,其实也没怎么吵啦,我们不大吵得起来的。然后我生气的说:不行,我不想看到你,今天晚上我要住旅馆去!然后呢,我就收拾东西,当然是假意思地收拾,心想我都在收拾东西了,你得过来拦着我拉着我啊——可他不来拦!我收拾完了以后,他说:这么晚你要走的话不安全,十点多了,我送你吧。然后我说:不用你送!然后他居然就递给我一张打折卡!他说:这个卡拿着,住酒店可以打折。——他不但不拦着,居然还递给张卡给我,让我住酒店时可以打折!当然最后没走成的,气得笑了,然后气就没了(笑)。
为什么大导演都在抢严歌苓的剧本?
樊海峰(水印书院创始人):我从商业的角度想问一个问题。这几年影视界出现了一个严歌苓现象,包括张艺谋等所有的大导演都在抢歌苓老师的剧本。所以希望请歌苓老师您从自身的角度解读一下,为什么你的作品那么多的大导演都会蜂拥而抢?
严歌苓:我记得陈凯歌有一次用了一个词叫“活色生香”形容我写的东西,有戏剧性啊或是矛盾在里面。或者说,其实好的电影,首先人物要塑造的好。过去我们看过很多特别过瘾的电影,都是人物特别好,像《简爱》里这两个人很有性格,还有《巴顿将军》这些,多好的性格,这才是经典电影。人物非常独特少有的性格,如果你通过银幕塑造出来的话,它好在不可重复。所以我写小说还是特别特别注重写人物,人物的性格是怎么通过一些细节展示出来。比如我前面讲的那个赌博的教授,那些细节里他展示的这种严谨,这种俭省就很好的塑造他的独特。
我觉得我在中国大陆得不了文学奖
樊海峰(水印书院创始人):昨天听歌苓老师讲她年轻时候的一些故事,讲到在成都的时候,很多你的同事战友,都去拜访自己的首长和领导,但是歌苓老师她从不参加,歌苓老师跟我说:“我从不这样,我只是把我的舞跳好,以硬碰硬。”你这句话非常我非常感动。我想问你以硬碰硬这个是源于你自己的家族的传承,还是你后来人生的一些经历影响?
严歌苓:不是拜访,就是提着什么东西去送给领导。比如她们的妈妈给她们寄吃的,她们会带去给那个首长,一到星期天就不见了这些人,小姑娘们都很有门路。以硬碰硬我觉得跟家族的传承有关系,我爷爷就是这么个人,我爸也是这么个人,都是比较清高的。他跟人的交往,不希望有利益在中间,只做真正的好朋友,一有利益他就变得非常的焦虑。
我到了海外也是,学习完了以后考上了研究生拿到了全奖学金,然后就开始给台湾写小说。因为那时候在台湾发表小说可以挣稿费,美金的稿费,大陆的那个稿费不行,是人民币。写了两三天以后,台湾报纸的副刊主编就和我说,我们有小说比赛,你来参加评选吧。后来我在台湾得的十个文学奖都是一等奖,一个二等奖叫《红罗裙》。他们评选的过程都是匿名,就是把所有作者名字隐藏变成编号,初审是大学的博士,二审呢就是一些作家,或者不是特别有名的评论家,三审就是特别有名的作家和评论家,比如王德威这样的人会参加三审。评选过程由始至终评委都是看不到作者名字的,我觉得这就叫硬碰硬。
如果在中国大陆评个文学奖那还得了,什么各种各样的去找关系啊什么的,各个省的作协也要去找,对吧?我觉得这就没劲了,那还有什么意思?所以我觉得我在中国大陆得不了文学奖,因为我从来不去找他们。
(座谈会结束,全文完)
座谈会后,严歌苓给读者签名
全球最美河流岸边的别墅与书院
水印长廊&水印书院,坐落于全球最美河流之一——漓江岸边,私享1.2公里漓江景观带,与桂林老八景“奇峰观月”隔江相望,与罕有白鹭栖息湿地——白鹭洲为邻。在探索山水精神、构筑具有山水意境的建筑载体的同时,也整合大师团队,希望能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季节带来自然美学体验与居住体验,倾力打造一种“诗意栖居”的生活。
声明:本文由入驻焦点开放平台的作者撰写,除焦点官方账号外,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,不代表焦点立场。